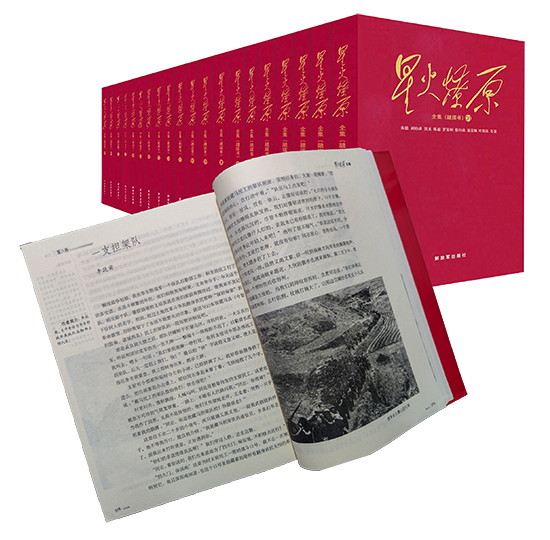
解放战争初期,我在华东野战军一个纵队后勤部工作,和支前民工打了许多交道。在战斗频繁的年代,他们和我匆匆相聚,又匆匆分手,今天这个队,明天那个队,像股汹涌的支前洪流在我们面前奔腾而过,使我来不及记下任何人的名字。然而,经过土地改革斗争的翻身农民那种“保田保家”的革命激情,却给我留下了永远不能磨灭的印象。就说与山东省藏马县(今划归胶南、诸城两县)民工担架队的一段短暂的相处吧。
那是孟良崮大捷之后,部队仍转辗于沂蒙山区,寻机歼敌。一天正在行军,听说和国民党军的另一张王牌——整编十一师相距不远了。后勤首长把我叫去,劈头一句话:“我们要到南麻一带打仗,你到支前司令部去领民工担架队,后天一定赶上我们。快!”最后的“快” 字说得又急又响,使人觉得任务非常紧急。我立即转身出来,跑步上路。
支前司令部那所临时办公的小房,已经挤满了人。我好容易侧身挤了进去,把公函塞到办公桌上,那位同志拿起来看了看,飞快地批了几个字,说:“藏马民工担架队拨给你们,快去领吧!”
村里村外,旗帜飘扬,人喊马叫,到处是整装待发的支前民工。这里也被急不可待的气氛笼罩着。一路上,不断有人拦路问我:“同志,你找谁?”当我作了回答,见我不是找他的,他们又失望地走开。正走着,突然一只手抓着我的胳膊:“同志,你是找藏马担架队的?快跟我走!”
这是位不出二十岁的小青年, 两只眼睛又黑又亮, 一副英武洒脱的样子。他不等我开口,就自我介绍:“我是藏马担架队的通信员,乡亲们等急了,派我出来打听消息,正好遇到你。”
“你们的求战情绪真高啊!”我们穿过人群,边走边聊。
“同志,看你说的,我们出来就是为了挡大门、保田地,不积极点还行!”
“挡大门,保田地”这是当时支前民工一致的战斗口号,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它,而且深深地知道:在这个口号里隐藏着的是所有翻身农民无穷的革命潜力。当我来到藏马民工担架队前面,说明任务后,大家一起喊着:“挡大门、保田地的决心,在行动中看”,“队伍马上出发吧!”
三伏天,没有一丝风,没有一块云。正像俗话说的:“七月的日头独头蒜”。火辣辣的太阳晒得皮肤发焦。我们好像钻进密封的匣子,口干舌燥,喘不过气来,头也昏沉沉的。尽管不断挥帽扇凉,汗水仍像泉水般地往外涌。我身旁有位老汉像汗人似的,走起来已有些摇晃了。我对他说:“老大爷,以后再有任务让年轻人来吧!”他听了很不服气:“你说这话不对。分田,我老汉有份;支前打老蒋,就没有份啦?同志放心,老将出马,一个顶俩。” 说完,便大踏步赶了上去。
民工们和老汉一样,虽然又渴又累,但一听到南麻方向传来的隆隆炮声,谁也不肯落后。离战场越来越近,大伙的脚步也越来越快。第二天下午,终于赶到我纵一个师的伤员收容所。战况是瞬息万变的,当我们到师收容所时,负责同志说:“你们来得正好。部队就要转移,去打临朐,仗越打越大了。山那边豆腐圩还有五十几名伤员,你们马上出发把他们抬回来,一刻不能耽搁!”
按说走了一天一夜,真是又累又饿,本当歇息一下,吃点东西,但面前的任务却要求我们一刻也不能耽搁。如果是部队倒也好办,我们常常几天不吃不睡,照样完成任务。可是民工不是部队呀!一位小队长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,他说:“走吧,这点苦算得了啥!别看我们是老百姓,可我们都是翻了身的人,觉悟高,有锻炼。”接着他告诉我,他们家乡是一边打仗一边土改的,地主武装经常来破坏骚扰,在田里干活也要站岗,搁下锄头打一仗是经常的事。
果然,我把眼前情况跟大家一摆,人群里立刻吵嚷起来:
“歇个啥,抬伤员要紧!”
“同志们为咱流血牺牲,咱少吃顿饭,少睡会觉算啥!”
到豆腐圩要经过一道山岭,荆棘漫腰,棱石满道,走起来十分吃力。走着走着,山谷里猛然卷起狂风,空气中夹杂着潮湿的气味,滚滚乌云迎头压来,震耳的雷鸣压过了山那边的枪声。不大一会瓢泼似的大雨兜头而下。这雨来得又急又猛,眨眼工夫,混浊的黄水从山上倾泻下来,仿佛一幅平面的大瀑布,漫着山坡从脚下流过。我们像在水面上行走,一步一滑,难上加难了。
本来队员都有件蓑衣,捆成小卷背在身上。昨天他们还夸耀这是宝贝:睡觉当褥子,天冷当皮袄,下雨是雨衣,哪用就哪到。可是现在,宁愿任雨浇淋,谁也没用。
翻过山来,天已黑定,空中星月不露,我们好像掉进染缸一样,伸手不见五指,只是借着雷电的闪光才找到了豆腐圩。许多房屋被敌人的炮火摧毁了,有的在冒着缕缕的白烟。部队已经开始转移,不声不响,迅速地从我们两旁擦身而过。
我正想打听一下消息,忽然有人压着嗓子问:“干什么的,有带队的吗?”我走出行列,那人把我拉到一旁,轻声告诉我:“我们要赶到临朐那边参加战斗。伤员就在圩子里,你们去抬吧,我们掩护,不过你们动作要快,别耽误了时间。”虽然天黑看不到他的神情,但从他那短促、兴奋的语调里,知道他在为未来的战斗激动着。
我十分理解时间在战斗中的意义,于是急忙带着担架队进村。
在一所没有完全坍塌的大房子里,找到了我们要抬的五十多位伤员。民工们不顾饥渴劳累,湿衣贴身,二话没说,一齐动手。外边又是一声沉雷,我猛然想到:如果伤员的伤口淋了雨,不仅要腐烂化脓,而且可能被破伤风菌侵袭,遭致生命危险。等雨停了再走?枪声告诉我们敌人离这儿已不远,而掩护部队又急着去执行另一个战斗任务。这时小通信员跑来催我:“都收拾好了,走吧!”我踌躇地说:“雨大,伤员的伤口怕淋!”“这不用你操心,伤员身上都盖上了蓑衣。”哦!难怪他们宁愿淋雨也不动蓑衣呢,原来早就准备好这手了。多么细心的人啊!我不由心里一阵滚热,满怀信心地说:“出发!”
我们冒雨离开村子,走不多远,前面队伍突然不动了。跑到前头一看,人们都在弯腰找路。糟啦,迷路了。我抬头四下望望,一片漆黑,辨不出东南西北,想点个亮照一照,又怕惹来敌人的炮弹。久停是不行的,只有按来的方向,不管有路无路走下去。
雨势渐渐小了一些,但是缠绵绵的,看不出休止的样子。道路比来时更加泥泞难行,民工们一步一滑地向前摇晃。估计离开豆腐圩有四五里路的样子,我的心才镇静下来,这时才发觉不知什么时候鞋子被泥拔去了一只,棱石划破了脚板,隐隐作痛。一天多水米没沾牙,肚子饿得咕咕直叫;湿淋淋的衣服贴在身上,只觉得浑身发冷。我不免想起那位老汉,年纪这样大,又抬着伤员,不知怎样艰难呢!但也想起他的话:“分田,我老汉有份;支前打老蒋,就没有份啦!”无论环境如何艰苦,老汉的腰杆是压不弯的。行列中静悄悄的,想必和老汉一样,都在小心翼翼地抬着伤员,默默地与饥渴疲劳作斗争。
谁知“房漏偏逢连阴雨”,走着走着,前面奇峰突起挡住了去路;本应向北,不知何时向西插来,倘钻进敌人窝去岂不要吃大亏!我急忙叫担架队往回走。
约摸又走了三四里路光景,开始向北爬山。这里的山坡更陡,上面覆着一层厚厚的稀泥,走一步滑回半步。人们抬着担架,拉着树枝杂草吃力地向上爬着,尽量不使自己摔倒给伤员增加痛苦。
爬过山腰,天色微明,地面依稀可辨,走路再也不像盲人骑瞎马那样摸索了。将到山顶,只见山峰像被神奇的巨斧砍去半边,两丈高的悬崖陡然而立,没有一线通路。崖壁峥嵘笔直,寸草不生,空手还可以攀登崖缝而上,担架却难以通过。
这时,枪声已经移到山脚下,敌人的喊声清晰可闻,可能是掩护部队正在转移。山上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。一个伤员躺在担架上说:“老乡们,你们为我们吃了千辛万苦,不能再拖住你们的腿了,到临朐去吧,那里有更重要的任务!”
民工们听了非常激动。小队长掀起一位重伤员的蓑衣,指着伤口对全体队员说:“乡亲们,这位同志负这样重的伤,为啥?还不是为了咱们。天大的困难,咱们也要把他们安全送到后方。”
“对,咱们不能搁下他们。”大伙异口同声地说。
小队长想了个办法:把伤员绑在担架上,再用绳子往上拉,虽然这要使伤员受点委屈,但再没有更好的办法了,大家立即行动。
天已经大亮,人们身上插满了伪装的树枝,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自报奋勇爬上悬崖,垂下几条绳子,套在担架上,然后用力往上拉。底下的人一手托着担架,一手攀登悬崖,往上护送。崖壁太滑,不时有人失足,担架保持不住平衡,碰到石崖,震痛了伤员的伤口。但伤员们咬着牙,忍着痛,没有一人吭声。
担架一抬一抬地吊了上去,一个小时之后,全体人员都爬上了悬崖。上面是一片空地,清查一下,伤员、民工一个不少。山下的枪声也停止了,大概掩护部队已经转移,正向临朐方向疾进!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,坐下来歇息。
这一夜,如同进行了一场恶战,民工们个个浑身是泥,许多人的衣服被山上的荆棘划破,有的划破手、脸,留着血迹。也有人在刚才拉担架时,手心被绳子磨得露出嫩肉。可是,他们似乎是习以为常,没事似的整理伤员身上的蓑衣,安慰伤员,然后又继续赶路。
当天下午,我们回到了师部收容所。担架队队员们胡乱吃点东西,又赶着去执行别的任务。我们共同战斗了一夜,就匆匆分手了。
像这样的民工担架队员,我遇到的太多了。他们为了保卫已得的胜利果实,为了自己的彻底解放,在“挡大门、保田地”的口号下,背井离乡,奔走在广阔的战场上,对革命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我虽然想不起他们的名字,但我常常想起那些翻身农民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革命激情,以及由这种革命激情而产生的力量。这个力量是我们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,赢得解放战争胜利的保证!
